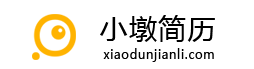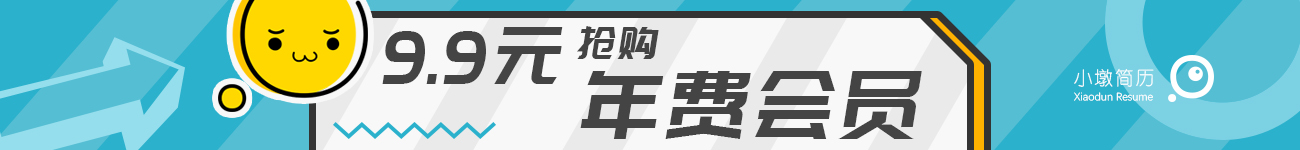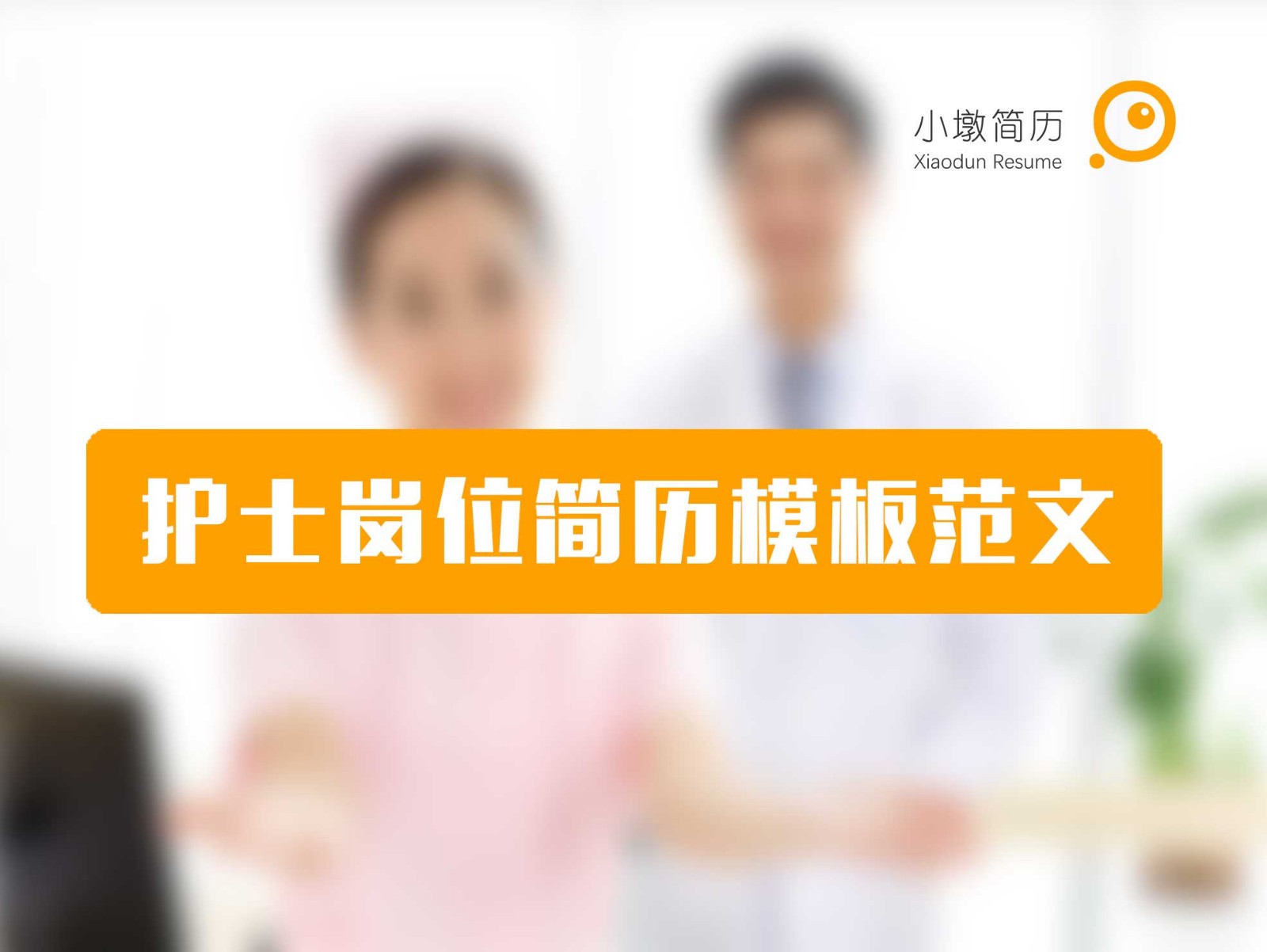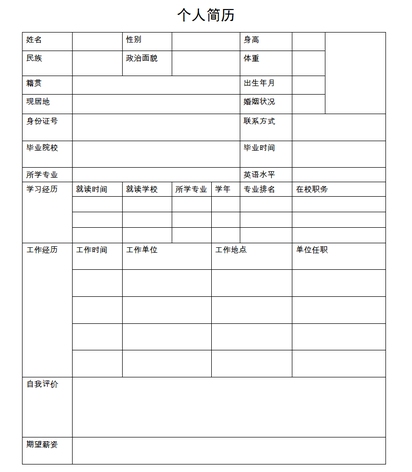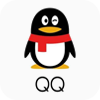根据统计学相关研究成果,我们得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20年内增长率高于5%时,年青一代才有可能比父辈更富有。那么,至少金砖四国尤其是中国,长期两位数增长,哪怕较为艰难2019、2020依旧能过维持在6%,理论上讲,至少90后应该感觉自己比60、70后更富有才对。但是,不仅是父辈觉得我们穷,我们也觉得我们穷,我们不是隐形贫困,我们是真穷。
穷,多翻译一句,就是挣得没有花的快、收入没有支出多,也就是说,你资不抵债。
扎心不,把自己欠的贷款、信用卡、花呗白条都捋一捋,再把所有的收入都放在一起,做个简单的加减法。

-
假资产太多
贷款和收入的清单好理,但是年轻人的资产负债表,是一笔自己都看不懂的糊涂账,年轻人最容易被披着资产外衣的负债所迷惑:
拥有的不一定是资产,很有可能是一种负债。
你贷款名牌车和你爹贷款买房,一个是负债,一个是资产。

-
狄德罗效应
贷款和收入的清单好理,但是年轻人的资产负债表,是一笔自己都看不懂的糊涂账,年轻人最容易被披着资产外衣的负债所迷惑:
拥有的不一定是资产,很有可能是一种负债。
你贷款名牌车和你爹贷款买房,一个是负债,一个是资产。
有多少人被前几年的消费升级忽悠了?
笔者曾在这个圈子浸淫许久,太了解整个行业是如何骗无知又物质的年轻人把钱花在升级上。
国货品质好价格低,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事,但是厂家和代理们可就发愁了,商品十年不坏,我的资金怎么回笼?
于是,一众新消费、中产消费、消费升级等包装下的新电商应运而生。
他们不会直接告诉你要买哪些东西,现在你的心里埋下一个小种子,告诉你即便不买房买车,总要买一款心仪的吹风机,头发跟自己一辈子(?),要对她好一点——从逻辑到实际都没毛病,你就下定决心买一款和广东外贸小厂品质一样的国际大品牌,1000-2000元,谁咬咬牙都能买得起。
紧接着,你就会不自觉的,洗脸仪,电动牙刷,加湿器,净化器,电子门锁,都要配齐。家里都整理的差不多了,对自己也要好一点呀?去油!保湿!美白!一个也不能少!最后,还要为知识付费,不买吴晓波和樊登的课程,怎么对得起精致的我!完美!
可是,你不能怪人家,人家只是告诉你买一件就可以,是你自己不断买买买。
关于这个,早在18世纪,发过哲学家狄德罗就已经警示过,可悲的是,300年来,没有哪一波年轻人逃得过「真香定律」:
有一天,朋友送他一件质地精良、做工考究的睡袍,狄德罗非常喜欢。然而,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:他穿着华贵的睡袍在书房走来走去时,总觉得家具破旧不堪、地毯的针脚也粗得吓人。为了与睡袍配套,旧的东西先后更新,书房终于跟上了睡袍的档次,可他却觉得很不舒服,因为“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了”。

-
无储蓄
中国人爱储蓄,被长期崇尚美国消费主义的人所鄙视,认为国人不会理财。
首先,储蓄就是理财的一种,否则你以为各国央行调整利率只针对大商业银行和企业贷款的吗?
退一步说,就算储蓄不算理财,那么,不理财,也是一种理财方式,只不过这种理财方式是按照通胀率定赔,就是每年都会按照通胀率贬值。
静态去看这件事,似乎赚了不储蓄太可惜了,但是遇到父辈们Bug级的操作——你禁不住人家经常有大量的本金加入,这一点年轻人总是以会花钱才会赚钱忽视掉——你忽视掉了,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和现金流。
会花钱才会赚钱,是你以投资自己为假设,这个是假设是基于你以工资作为主要收入,工资又是什么呢?——在社会主义国家,工资不存在剥削的问题,但是存在自我剥削、时间剥夺的等效关系,你再怎么折腾都是在尽可能的榨取自己的剩余价值。
你知道吗?你的赚钱速度永远不会高于资本的赚钱速度。
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在你遇到好的项目时,拥有足够多的钱。
但是,年轻人,你太会花钱了,你没有充足的资金可以利用。

-
稳定和不稳定都是错
父辈,大多数人很稳定,一辈子赚不到大钱,你看不起;一部分50后、60后下海经商,从不稳定中赚到了钱,你只看到了钱,却想过20后、30后、40后、50后、60后、70后,几代人的稳定而辛勤的劳作才换来了某一波人的机会。
同学,靠不稳定来赚取高收益的时代早就过去了。
那我们的不稳定是什么呢?
大家听说过「低水平重复建设」吧!
动不动就要出去看看的年轻人,每个两三年、甚至几个月就像DC和X战警世界一样,动不动就会给你重启一下,怎么可能和十年布局的「复仇者联盟」的吸金能力相提并论?
你总是在怀疑中接收一份工作、怀疑能力和同事、每天幻想着外面的世界,最终某一天情绪跌到谷底就裸辞了,本以为可以像网红一样去旅个游,但目标从欧美、到日本、到新马泰、到北戴河、到阿那亚,一降再降之后,你终于知道,我应该回去了工作了。然后,又来:怀疑中接收一份工作、怀疑能力和同事、每天幻想着外面的世界……
你离着更好的生活,总差那么一道坎。
比这种盲目寄希望于不稳定的人更可悲的是消失在稳定中的一群人。
当然,更多人生活在一种隐形的辞职中,就是它不是真的辞职了,而是在三十岁的某一天,再也不想工作这件事了,工作不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,而是他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。
这两类人最可悲的是,人生从未触底,也从未到达过天花板。